日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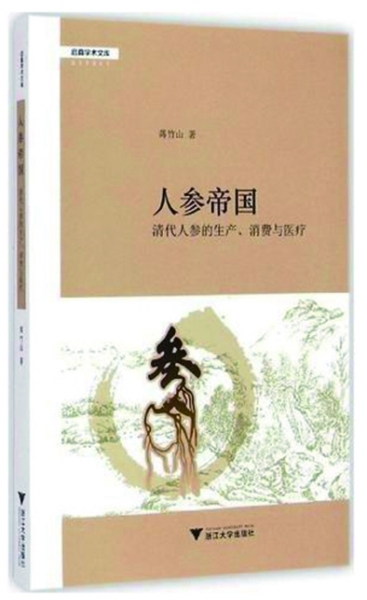
制度设计虽严密,但依然逃不了官僚化的缺陷。面对资源耗尽,采参成本的增加,偷盗、逃匿始终难以做到有效管理,官员与地方势力的勾结,牟取私利,大面积人参挖掘和秧参(种植物)与含铅的泡丁充斥,高丽参浸润矾糖水增重,以致现有的山参不足以供应到消费市场,凸显出专制垄断经济的特征。在流通、消费市场,江南的温补文化是人参消费增加的主要原因;人参价格因当时负责销售的重要机构和内务府哄抬而价格高昂;人参专书的出现可以看到江南参商成功地塑造了几个重要的品牌,完成了从生产到消费的流通闭环。蒋先生以此反省到人参的研究不仅应该是地区的历史,更应放在全球史的视野下扩展到朝鲜、日本甚至北美的人参贸易。
蒋先生作为新文化史的重要推手,引介理论,评论著作颇有贡献。架构的新文化史工作坊、新文化史部落格则多有宣导意义。在新文化史实践上对人参研究从博士论文开始到现在,较有创见。就本书来说,我们至少可以看到值得称赞的特征,这无疑是对国内研究一个重要的启发。
第一,物质文化史视角的分析。这受Daniel Roche 影响,重视社会与文化分析方法、私人生活和公共生活的迫切需要以及物质文化中选择行为所体现的准则。这表现在文章中对流通与消费关系的分析。另外的重要贡献是分析江南温补文化对人参消费的刺激。第二,新资料的扩展。蒋先生通过对大内档案的阅读,理清了参务细节上的不少问题。比如说,通过《雍正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的解读,发现了雍正皇帝打破官方长期垄断,开放民间采人参,这对探索参务政策全貌增添了细节;将医案、医书纳入解释范围,构建江南温补用药的情况。第三,通过考辨前人研究成果的细节,在人参贩卖制度实践的变化中发现了内务府在贩卖人参过程中的角色。通过秧参案,看到了国家权力对人参采集的全面介入。对商人贩卖官参的过程分析得比较细致,多有贡献。
不过书的内容还是颇有值得商榷的地方,人参生产过程中,作者忽视了私挖人参对政策影响的深入探讨。这个环节之所以重要,是因为他还会影响到下游的消费市场。这里可以提供的数据从人数到规模都是惊心的:康熙三十三年奉天将军衙门咨盛京包衣佐领称“去宁古塔乌拉等处偷挖人参之人一年将及三四万,马牛达七八万。前去无业之人,在山居住一年需食七八石”,这达到合法采参的六倍。
而在数量上,可以见诸已有统计的雍正二年八十五点三两,三年一千六百零二点八两,七年一百九十八点一两,九年九千二百三十六点八两,十年十一年两年内数量超过九千两,十二年五千一百九十点六两,十三年两千余两,乾隆六年四千两,二十四年偷买三千二百七十二两,宁古塔一千零四十五两,以乾隆二十四年入库人参五百四十六点一六斤计,盗采接近人参的一半(《雍正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黑图档》《清高宗实录》)。
而这些数据仅仅是浮在表面,根据李博先生估计分析,每个链条各个环节利润,盗采占百分之四十,飞参人员占百分之二,剩余被参商和官员瓜分(李博《清代顺治至嘉庆时期东北地区的私参活动》)。蒋在人参的贸易、价格与流通一章上有些许铺陈私参流通的问题,但是没有做进一步分析。私参与官僚体系共长,对制度与市场的影响究竟如何?这需要制度经济学的分析才有较为清晰的图像,这甚至可以影响到蒋书对秧参的讨论。
因为整个政治经济运作体系不清晰,各种角色的博弈合作缺少有效分析,其实很难如蒋所说,“到了嘉庆朝,现有的山参已经无法供应广大的江南消费市场,取而代之的是秧参逐渐取代山参,成为下一波参务改革的导火线。”(113页)大量种植秧参的动力,未必只是文献上所揭示的上缴压力和市场需求原因,为何不是官、商共谋山参的结果?蒋书从整体的建构来看,从生产到消费缺乏有效的分析的框架,逻辑关联不够。因为没有密切的关系数据、曲线分析,我们是很难看到相关性的。价格、税收、通货膨胀、政策、消费等如何同其相关的?交易成本、博弈关系如何发挥作用的?如果缺失这个环节,十分容易陷入某点影响结果的误区。
同样在流通、消费环节,一是缺乏其他地区的情况比照,私参毕竟也流通到山西、山东和广东(213页);二是缺少结合对江南经济史的观察来理解人参的消费。
在流通过程中,人参变价的事情,笔者还搜集到其他资料,以丰富人参变价与地方经济的交互影响,这些蒋书略过,实有重要问题可以探讨,以深刻理解人参流通中的实际情形。陶澍接管人参变价任务后发现:“查两淮奉发变价参斤已欠五年价银未缴,其各年未缴价银内丙戌、丁亥两年除已解外,仍未缴银三十四万两千六百四十两三钱,戊子年未缴银二十一万四千六百九十两八分,己丑未缴银二十万九千九百九十三两四分,庚寅未缴银十九万六千六百八十四两四钱,以上共该银九十六万四千七两八分二分。”(《陶云汀先生奏疏》)
而这件事情与当时实际盐政关联颇多,两淮在变卖方式上是售卖于盐商,即为“派于下纲引内征解”,但是因为私盐太盛,无人征解,于是只能挪用不够充盈的库款。内务府担心拖欠的连锁反应,震慑之下,凑请一分生息。经过陶的博弈之后才取消决定。直到最后才减轻任务,但仍然申斥两淮以及粤海关“当认真督促,以限解交清年款,不准任意拖延,稍有蒂欠以应支发”。鸦片战争战争后,广东的危机也因为经济的影响,变价十分艰难。滕德永先生通过研究道光朝内务府人参变价的困难认识到,道光朝人参变价的困境,是整个清王朝经济衰败的结果。
那么在人参的消费中,又是怎样的状况呢?比如清代乾隆到嘉庆时期,江南物价上涨的因素或多或少成为人参价格变化的原因,因而论述消费文化影响似乎还不能排除有人参销售本身刺激文化生成的可能。这还需要对医学史各派情况的熟悉,对医生与人参销售、文化传播因素的考量。同样不能忽视礼物文化(书已提到)、巫术、宗教建构对人参形象的建构,这些都可以成为消费因素而被商家利用。
总体来说,我们还不能想象人参在生产到消费这个过程是如何关联起来的。假如说各自成篇而为论文集,贡献还是很大的。
另外,豆瓣朋友对第八章内容吐槽甚多,此不一一列举。我看此章标题是“从人参史反思全球视野下的医疗史研究”,而具体内容从第241页以后,与人参史全然无关。这个算不上反思,只是将作者之前发表的《“全球转向”:全球视野下的医疗史研究初探》一文代入,用来作为本书的结论性章节,不太合适。 ■
蒋竹山博士的《人参帝国》读竟,觉得不错,便积极地与朋友分享。在浸会大学担任生药学教职的老友Eric兄发来一妙论:历史学者涉足中医药与中医药学者研究历史,似各有千秋。
本书的特点,璞庵兄长篇书评颇为中肯,不劳我费辞。诚如Eric所言,蒋博士以历史学家身份涉足中医学术,固然难能可贵,但本草毕竟是专学,行外人拈举,总难免偏谬,这些错误或许不伤主体结论的正确,仍以矫正为宜。不贤识小,此之谓也。
 人参的名实
人参的名实
研究本草,名实是绕不开的问题,药名所对应的物种,在不同时期、不同地域,乃至不同作者的笔下,都有可能不同,此即所谓的“同名异物”。
人参是本书的研究对象,作者有明确定义:“人参在中国的应用已有相当久远的历史,其英文学名是Panax Ginseng C. A. Meyer。”(25页)首先订正,这是人参的拉丁学名,还未听过“英文学名”一说,正确的书写格式应该是Panax ginseng C. A. Meyer。至于人参的英文名,就是ginseng;药材的英文名,《中国药典》使用的是Ginseng Radix et Rhizoma。
但传统文献中出现的人参词汇,并不都对应五加科的Panax ginseng,如《吴普本草》说:“或生邯郸,三月生,叶小锐,枝黑,茎有毛。三月、九月采根。根有头足手,面目如人。”(此据《太平御览》卷九百九十一,本书第26页转引自《人参谱》,文字有所篡改,且谬标点为:叶小,锐枝,黑茎有毛。)这种“人参”,虽然不明品种,但显然不是五加科植物。
又如《本草经集注》说:“上党郡在冀州西南,今魏国所献即是,形长而黄,状如防风,多润实而甘,俗用不入服,乃重百济者,形细而坚白,气味薄于上党。次用高丽,高丽即是辽东,形大而虚软,不及百济。”本书亦引此,并结论说:“由此可见人参在当时,最好的等级是百济产地,其次才是上党及高丽。”(27页)作者可能没有想到,今天生药学家倾向于认为,这种上党郡所出,由魏国献来,“形长而黄,状如防风,多润实而甘”的人参,其实是桔梗科植物党参Codonopsis pilosula(谢宗万,《中药材品种论述(上册)》,1990年,87页)。
作者不了解同名异物,而另一方面,又把一些古人已经分开的概念,搅合在一起。“参”在本草中是个集合概念,《神农本草经》有六种参,分别是人参、沙参、丹参、玄参、苦参和紫参,各自为条。本书有这样的议论:“《本草纲目》有关人参的记述分在草部的十二、十三卷。十二卷有人参、沙参、玄参、丹参、紫参,十三卷有苦参。”(41页) 其后图表2-2.1“《本草纲目》《本草从新》《本草纲目拾遗》中的人参分类比较表”(48页),同样将沙参、丹参、玄参等《本草经》原有药物,土人参、煤参、党参等新增品种,全部混入“人参”概念中,这可算是把自己的疏谬强加给古人。
上党人参与辽东人参
在古代文献中,辽东是仅次于上党的人参产地,《名医别录》云:“人参生上党山谷及辽东。”苏东坡《小圃五咏·人参》也说:“上党天下脊,辽东真井底。”作者总结说:“明中叶以前,辽参并非是最受欢迎的人参,山西上党人参的知名度甚至高过辽参。”(23页)其说不误,但上党人参资源枯竭的时间,以及辽东人参在明代以前未能“受欢迎”的原因,未必尽如作者所论。
梁代上党人参已不多见,陶弘景在《本草经集注·序录》中感叹说:“上党人参,世不复售。”而人参条正文描述魏国送来的上党人参,其实更像是桔梗科的党参。本书作者在《证类本草》中读到这句话,竟因此得结论说:“该书(指《证类本草》)另外提到‘上党人参,世不复售’,可见到了宋代,上党人参的产量可能已经因过度开采的缘故而日渐减少。”(30页)
唐代官修的《新修本草》绝口不提辽东人参,实别有隐情。《新修》成于高宗显庆二年(659),而在总章元年(668)高丽被灭,唐政府在今平壤设置安东都护府以前,辽东大部是被高丽占领,乃至唐太宗曾感叹说:“辽东旧中国之有,自魏涉周,置之度外。隋氏出师者四,丧律而还,杀中国良善不可胜数。”语见《册府元龟·帝王部·亲征二》。这样一来,唐代官方及民间人士,如《新修本草》《药性论》《茶经》等不愿意表扬辽东人参,也就容易理解了。
北宋时期,辽东人参因产于辽朝疆域内的女真人控制地区,中原难于得到。《本草图经》《本草衍义》都承认,当时人参主要从河北榷场博易,以及由海路进口。宋代文献推崇本国出产的上党人参,乃至以上党紫团山特产紫团参为至宝(紫团参见本书第31页),更多的是出于“爱国主义”情结。
特别有意思的是,在苏颂编撰《本草图经》后不足百年,包括上党在内的整个北方地区落入女真之手,建立金朝。金代刘完素(1120-1200)《黄帝素问宣明方论》卷九仙人肢丸,人参与紫团参同用;稍晚的元代赵州(今河北赵县)王好古(约1200-1264)《医垒元戎》卷十二紫苑丸,治五种风癞之疾,也同时使用紫团参与人参。刘、王二人的家乡离上党不远,刘完素的时代距《本草图经》成书更近,而皆意识到所谓上党紫团参与人参不同,这决不能用从宋到金百年之间上党Panax ginseng被采挖殆尽,且已经用Codonopsis pilosula冒充来解释之。所以我甚至怀疑,紫团参其实就是桔梗科的党参,而北宋提倡紫团参还有更深的内幕有待发掘(王家葵,《中药材品种沿革及道地性》,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2007年)。
本草文献
作者不熟悉本草著作的文献源流,许多本草文字都从清代陆烜《人参谱》中转引,误会甚多。
本书两处引用陶弘景的《药总诀》(27页)。按,今本《华阳陶隐居集》有陶弘景撰《药总诀序》一篇,此书《崇文总目》《通志》皆作一卷,《宋志》名《制药总诀》一卷,均不著撰人,《通志》别有《陶隐居集药诀》一卷。据《证类本草·卷一》“(嘉祐)补注所引书传”云:“《药总诀》,梁陶隐居撰,论次药品五味寒热之性,主疗疾病,及采畜时月之法,凡二卷。一本题云《药像敩诀》,不著撰人名氏,文字并相类。”则知此书宋代尚存,今则仅存序文,另外,《证类本草》镜鼻、石蚕、马蹄、水牛角、牡鼠等五条存《嘉祐本草》引《药诀》佚文,《医心方》卷一引《药像敩》一条。本书所引,实出于《本草经集注》,被《人参谱》误标为《药总诀》。
又引用五代李珣的《南海药谱》(28页)。据“(嘉祐)补注所引书传”云:“《南海药谱》,不著撰人名氏,杂记南方药所产郡县,及疗疾之验,颇无伦次。似唐末人所作,凡二卷。”《本草纲目》说:“此即《海药本草》也,凡六卷,唐人李珣所撰。”将《南海药谱》等同于《海药本草》是李时珍的一家之言,核查这段引文,见于《证类本草》人参条引《海药本草》,本书从《人参谱》标注为“李珣《南海药谱》”。
经史文献之误引
本书在本草文献上的疏谬,多数属情有可原者,真正让我下决心写这篇批评意见的,是看到作者对常见经史文献的误引。
关于《急就篇》,作者说:“西汉的《急就章》也记有:‘远志主益智惠而强志,故以为名,一名要绕、一名棘冤,其叶名小草,亦目其细小也;续断一名接骨,即今所呼续骨木也;又有续断,其华细而紫色根,亦入药用;参谓人参、丹参、紫参、沙参、苦参也;土瓜一名菲,一名芴。’”(26页)脚注提示,这段文字引自日人今村鞆著《人参史》,我没有读过此书,但总算抄写过《急就章》,知道第二十四章最末两句是:“远志续断参土瓜,葶苈桔梗龟骨枯。”作者引录的是颜师古注文,且标点、文字皆有错漏。
关于《说文》,作者说:“参的古字是‘參’,东汉许慎《说文解字》对‘参’字的演变的描述:‘参,人参,药草,出上党。’”(26页)脚注提示出处是段玉裁《说文解字注》。《说文》其实是这样说的:“薓,人薓,药草,出上党。”关于“薓”字的演变,《本草纲目》人参条释名项说得非常好:“人薓年深,浸渐长成者,根如人形,有神,故谓之人薓、神草。薓字从薓,亦浸渐之义。薓即浸字,后世因字文繁,遂以参星之字代之,从简便尔。然承误日久,亦不能变矣,惟张仲景《伤寒论》尚作薓字。”今天看到《五十二病方》中的“苦参”即写作“苦浸”,“浸”即是“薓”的省写;阜阳万物汉简紫参写如“紫薓”。可知李时珍所说不谬。
按,“薓”本来是人参的专名,故《说文》以人薓释薓。但汉代药用的“薓”字多数已经简写为“参”,不仅《急就篇》作“远志续断参土瓜”,《本草经》六参皆用“参”字,东汉武威医简中苦参、人参也使用“参”字。“薓”简写为“参”,可能仍与人参有关。《说文》“参,商星也”,据段玉裁说当为晋星,《周礼·春官》“实沈,晋也”,皆以参星为晋地的分野,汉代记载人参的产地皆为山西上党,《说文》云“出上党”,《本草经》言“生上党山谷”,《范子计然》亦云:“人参出上党,状类人者善。”又《春秋运斗枢》言:“揺光星散为人参,废江淮山渎之利,则摇光不明,人参不生。”由此可知汉代“人参”之得名,确与天上星宿有关,则“参”字亦可能暗示产地,特指晋地的上党。 ■
本书的特点,璞庵兄长篇书评颇为中肯,不劳我费辞。诚如Eric所言,蒋博士以历史学家身份涉足中医学术,固然难能可贵,但本草毕竟是专学,行外人拈举,总难免偏谬,这些错误或许不伤主体结论的正确,仍以矫正为宜。不贤识小,此之谓也。

研究本草,名实是绕不开的问题,药名所对应的物种,在不同时期、不同地域,乃至不同作者的笔下,都有可能不同,此即所谓的“同名异物”。
人参是本书的研究对象,作者有明确定义:“人参在中国的应用已有相当久远的历史,其英文学名是Panax Ginseng C. A. Meyer。”(25页)首先订正,这是人参的拉丁学名,还未听过“英文学名”一说,正确的书写格式应该是Panax ginseng C. A. Meyer。至于人参的英文名,就是ginseng;药材的英文名,《中国药典》使用的是Ginseng Radix et Rhizoma。
但传统文献中出现的人参词汇,并不都对应五加科的Panax ginseng,如《吴普本草》说:“或生邯郸,三月生,叶小锐,枝黑,茎有毛。三月、九月采根。根有头足手,面目如人。”(此据《太平御览》卷九百九十一,本书第26页转引自《人参谱》,文字有所篡改,且谬标点为:叶小,锐枝,黑茎有毛。)这种“人参”,虽然不明品种,但显然不是五加科植物。
又如《本草经集注》说:“上党郡在冀州西南,今魏国所献即是,形长而黄,状如防风,多润实而甘,俗用不入服,乃重百济者,形细而坚白,气味薄于上党。次用高丽,高丽即是辽东,形大而虚软,不及百济。”本书亦引此,并结论说:“由此可见人参在当时,最好的等级是百济产地,其次才是上党及高丽。”(27页)作者可能没有想到,今天生药学家倾向于认为,这种上党郡所出,由魏国献来,“形长而黄,状如防风,多润实而甘”的人参,其实是桔梗科植物党参Codonopsis pilosula(谢宗万,《中药材品种论述(上册)》,1990年,87页)。
作者不了解同名异物,而另一方面,又把一些古人已经分开的概念,搅合在一起。“参”在本草中是个集合概念,《神农本草经》有六种参,分别是人参、沙参、丹参、玄参、苦参和紫参,各自为条。本书有这样的议论:“《本草纲目》有关人参的记述分在草部的十二、十三卷。十二卷有人参、沙参、玄参、丹参、紫参,十三卷有苦参。”(41页) 其后图表2-2.1“《本草纲目》《本草从新》《本草纲目拾遗》中的人参分类比较表”(48页),同样将沙参、丹参、玄参等《本草经》原有药物,土人参、煤参、党参等新增品种,全部混入“人参”概念中,这可算是把自己的疏谬强加给古人。
上党人参与辽东人参
在古代文献中,辽东是仅次于上党的人参产地,《名医别录》云:“人参生上党山谷及辽东。”苏东坡《小圃五咏·人参》也说:“上党天下脊,辽东真井底。”作者总结说:“明中叶以前,辽参并非是最受欢迎的人参,山西上党人参的知名度甚至高过辽参。”(23页)其说不误,但上党人参资源枯竭的时间,以及辽东人参在明代以前未能“受欢迎”的原因,未必尽如作者所论。
梁代上党人参已不多见,陶弘景在《本草经集注·序录》中感叹说:“上党人参,世不复售。”而人参条正文描述魏国送来的上党人参,其实更像是桔梗科的党参。本书作者在《证类本草》中读到这句话,竟因此得结论说:“该书(指《证类本草》)另外提到‘上党人参,世不复售’,可见到了宋代,上党人参的产量可能已经因过度开采的缘故而日渐减少。”(30页)
唐代官修的《新修本草》绝口不提辽东人参,实别有隐情。《新修》成于高宗显庆二年(659),而在总章元年(668)高丽被灭,唐政府在今平壤设置安东都护府以前,辽东大部是被高丽占领,乃至唐太宗曾感叹说:“辽东旧中国之有,自魏涉周,置之度外。隋氏出师者四,丧律而还,杀中国良善不可胜数。”语见《册府元龟·帝王部·亲征二》。这样一来,唐代官方及民间人士,如《新修本草》《药性论》《茶经》等不愿意表扬辽东人参,也就容易理解了。
北宋时期,辽东人参因产于辽朝疆域内的女真人控制地区,中原难于得到。《本草图经》《本草衍义》都承认,当时人参主要从河北榷场博易,以及由海路进口。宋代文献推崇本国出产的上党人参,乃至以上党紫团山特产紫团参为至宝(紫团参见本书第31页),更多的是出于“爱国主义”情结。
特别有意思的是,在苏颂编撰《本草图经》后不足百年,包括上党在内的整个北方地区落入女真之手,建立金朝。金代刘完素(1120-1200)《黄帝素问宣明方论》卷九仙人肢丸,人参与紫团参同用;稍晚的元代赵州(今河北赵县)王好古(约1200-1264)《医垒元戎》卷十二紫苑丸,治五种风癞之疾,也同时使用紫团参与人参。刘、王二人的家乡离上党不远,刘完素的时代距《本草图经》成书更近,而皆意识到所谓上党紫团参与人参不同,这决不能用从宋到金百年之间上党Panax ginseng被采挖殆尽,且已经用Codonopsis pilosula冒充来解释之。所以我甚至怀疑,紫团参其实就是桔梗科的党参,而北宋提倡紫团参还有更深的内幕有待发掘(王家葵,《中药材品种沿革及道地性》,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2007年)。
本草文献
作者不熟悉本草著作的文献源流,许多本草文字都从清代陆烜《人参谱》中转引,误会甚多。
本书两处引用陶弘景的《药总诀》(27页)。按,今本《华阳陶隐居集》有陶弘景撰《药总诀序》一篇,此书《崇文总目》《通志》皆作一卷,《宋志》名《制药总诀》一卷,均不著撰人,《通志》别有《陶隐居集药诀》一卷。据《证类本草·卷一》“(嘉祐)补注所引书传”云:“《药总诀》,梁陶隐居撰,论次药品五味寒热之性,主疗疾病,及采畜时月之法,凡二卷。一本题云《药像敩诀》,不著撰人名氏,文字并相类。”则知此书宋代尚存,今则仅存序文,另外,《证类本草》镜鼻、石蚕、马蹄、水牛角、牡鼠等五条存《嘉祐本草》引《药诀》佚文,《医心方》卷一引《药像敩》一条。本书所引,实出于《本草经集注》,被《人参谱》误标为《药总诀》。
又引用五代李珣的《南海药谱》(28页)。据“(嘉祐)补注所引书传”云:“《南海药谱》,不著撰人名氏,杂记南方药所产郡县,及疗疾之验,颇无伦次。似唐末人所作,凡二卷。”《本草纲目》说:“此即《海药本草》也,凡六卷,唐人李珣所撰。”将《南海药谱》等同于《海药本草》是李时珍的一家之言,核查这段引文,见于《证类本草》人参条引《海药本草》,本书从《人参谱》标注为“李珣《南海药谱》”。
经史文献之误引
本书在本草文献上的疏谬,多数属情有可原者,真正让我下决心写这篇批评意见的,是看到作者对常见经史文献的误引。
关于《急就篇》,作者说:“西汉的《急就章》也记有:‘远志主益智惠而强志,故以为名,一名要绕、一名棘冤,其叶名小草,亦目其细小也;续断一名接骨,即今所呼续骨木也;又有续断,其华细而紫色根,亦入药用;参谓人参、丹参、紫参、沙参、苦参也;土瓜一名菲,一名芴。’”(26页)脚注提示,这段文字引自日人今村鞆著《人参史》,我没有读过此书,但总算抄写过《急就章》,知道第二十四章最末两句是:“远志续断参土瓜,葶苈桔梗龟骨枯。”作者引录的是颜师古注文,且标点、文字皆有错漏。
关于《说文》,作者说:“参的古字是‘參’,东汉许慎《说文解字》对‘参’字的演变的描述:‘参,人参,药草,出上党。’”(26页)脚注提示出处是段玉裁《说文解字注》。《说文》其实是这样说的:“薓,人薓,药草,出上党。”关于“薓”字的演变,《本草纲目》人参条释名项说得非常好:“人薓年深,浸渐长成者,根如人形,有神,故谓之人薓、神草。薓字从薓,亦浸渐之义。薓即浸字,后世因字文繁,遂以参星之字代之,从简便尔。然承误日久,亦不能变矣,惟张仲景《伤寒论》尚作薓字。”今天看到《五十二病方》中的“苦参”即写作“苦浸”,“浸”即是“薓”的省写;阜阳万物汉简紫参写如“紫薓”。可知李时珍所说不谬。
按,“薓”本来是人参的专名,故《说文》以人薓释薓。但汉代药用的“薓”字多数已经简写为“参”,不仅《急就篇》作“远志续断参土瓜”,《本草经》六参皆用“参”字,东汉武威医简中苦参、人参也使用“参”字。“薓”简写为“参”,可能仍与人参有关。《说文》“参,商星也”,据段玉裁说当为晋星,《周礼·春官》“实沈,晋也”,皆以参星为晋地的分野,汉代记载人参的产地皆为山西上党,《说文》云“出上党”,《本草经》言“生上党山谷”,《范子计然》亦云:“人参出上党,状类人者善。”又《春秋运斗枢》言:“揺光星散为人参,废江淮山渎之利,则摇光不明,人参不生。”由此可知汉代“人参”之得名,确与天上星宿有关,则“参”字亦可能暗示产地,特指晋地的上党。 ■








